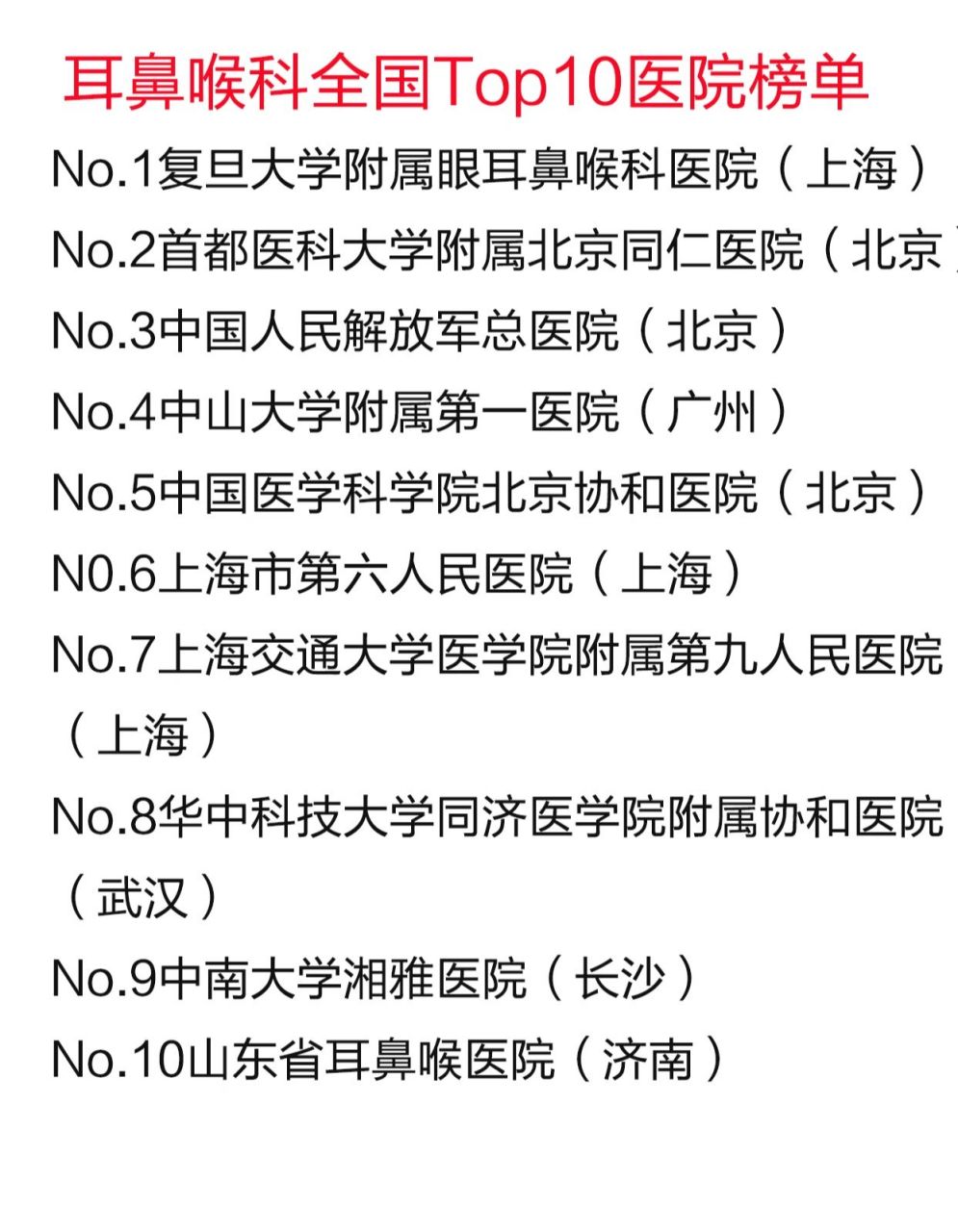▲ 从大厂裸辞后,拉拉和丈夫在北京延庆区井庄镇三司村租下一间小院子,远离市区住了两年。(受访者供图 / 图)
全文共6180字,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
那时的上司常常告诫他,人生就是应该拼命向上爬、拼命挣钱。离职后,这位前上司给他打电话,问了一个问题:“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获得快乐?”
张默每天都工作到很晚,有时候花七八个小时打磨一个物件,或者用十天甚至更长时间做一把椅子、一张桌子。他享受这个过程。学木工之后,师傅对他说,“人生很漫长,偶尔暂停一下其实也没什么。”
比起在大厂,他的收入水平大幅滑落,存款几乎没有增加,只能维持简单的生活开支。
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
文|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
南方周末实习生 温若梅
责任编辑|李慕琰
辞去互联网运营总监的工作后,张默做起了木工。他在浙江东阳一间木工学校敲了十个月木头,这件事很枯燥,但一做起来就容易废寝忘食。有一次,他花八九天时间做了一个木马,纯粹只是因为想做。
张默觉得木头很有温度,相较于和人相处,他更享受和物相处的时光,在对木头的锉磨中,他找到让自己安定下来的方式。
以前在互联网公司,他曾是一条业务线的运营总监,拿着比同龄人高的薪水,在上海贷款买了房,在安徽老家的亲友眼里,他是成功人士。然而公司复杂的组织架构、林立的派系、漫长的审批流程让他束手束脚,无止尽的加班、两点一线的通勤生活也让他感到疲惫。
那时的上司常常告诫他,人生就是应该拼命向上爬、拼命挣钱。离职后,这位前上司给他打电话,问了一个问题:“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获得快乐?”
很多年轻人正在离开大厂。
脉脉研究院发布的《2023职场迁徙报告》显示,2022年,互联网职位量同比减少50.4%,28.19%职场人跳槽或主动离职,9.42%被裁。
高薪曾经是吸引年轻人涌入大厂的主要原因之一,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各行业平均工资情况显示,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年收入为21.3万元,超出第二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6万多元。
然而,当行业泡沫退去,一些年轻人发现,高薪并不意味着高幸福指数,“内卷”、工作生活的不平衡带来的精神消耗等影响着他们的选择。疫情之后,越来越多人开始渴望安稳、在工作的缝隙中找回生活。
离开大厂之后,他们去了哪里?
辞去互联网运营总监的工作后,张默做起了木工。(受访者供图 / 图)
“这个行业发展很快,不会等你”
疾病让前大厂人拉拉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。
拉拉1982年出生,曾就职于百度的职能部门,工作性质接近高层领导的助理。2020年底,她被查出宫颈病变,做了手术。术后恰逢疫情封控,但她发现居家办公的压力更大了,工作时长没有减少,只是省去了通勤时间,相当于一睁眼就在办公,一直到睡觉,同事和领导没有太考虑到她是一个尚需休养的病人。
拉拉同在互联网大厂的丈夫也遭遇了职业瓶颈。换了几个团队后,他意识到互联网行业对35岁以上的人不太友好。和父母沟通后,两人一起裸辞了。拉拉为此放弃了剩下两年的股权激励。
2017年,奶盖经由校招进入一家游戏行业头部大厂做直播运营。那时大厂在毕业生眼中是一片沃土,光鲜、体面,她至今仍然怀念公司包容宽松的气氛:可以穿Lolita上班,染花里胡哨的头发,“没人管你”。
奶盖和男朋友感情稳定,毕业后都进入互联网行业。不久,家里开始催婚,他们考虑未来:加班严重,如果两人都在这个行业,以后可能无暇照顾家庭。公司正常下班时间是晚上7点,但没有人7点走,即使没什么事,大家也会拖到9点以后;有事情做的时候,加班到10点、11点是常事。
让奶盖更为触动的是一位女同事,曾经单枪匹马干到管理层,但当她休完半年产假,再回到原来岗位时,发现她之前的业务已经被瓜分掉,只能做一些边缘工作。奶盖考虑,如果不结婚,也许可以继续待下去,一旦要结婚,面临家庭和工作的权衡,“这个行业发展很快,不会等你”。
在工作上,奶盖也开始感到吃力。大厂的薪水里,绩效是大头,有的同事能翻倍完成KPI,拿到高她一倍的工资,自己却只能勉强完成指标。父母也不支持她在这个行业久待,他们常念叨,让她换一份稳定、清闲的工作。多方因素驱使下,2020年8月,奶盖提出了离职。
35岁的西西则是被动离职。她毕业就进入互联网行业,后来做电商运营,担任一个三十余人团队的小组长,2022年3、4月起,领导开始找她沟通部门裁员的事宜,身边的同事开始一个个离开。最终,她所在的部门和另一个部门合并,整个核心运营团队都被裁员,只留下了四五个客服和采购。这批被裁掉的人中也包括她自己。
西西的朋友颜子车比她小三岁,上一份工作是某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电商运营,2021年入职时,整个项目还在扩招,一年之后很多业务开始被砍掉,他在被“优化”之列,幸运的是领到了裁员补贴——他戏称为“大礼包”。
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,西西和颜子车都已待业大半年。
虽然回到了城市,拉拉的小院至今还在出租,每周邀请不同的朋友去小院里过周末。(受访者供图 / 图)
“偶尔暂停一下其实也没什么”
离职的决定是2019年底做出的,那年张默28岁。辞职后,他陷入情绪和事业的低谷期,原本准备出国留学,但因疫情受阻。他是学建筑设计出身,在尽力重拾生活热情的迷茫期里,他想到了学木工。
2020年,他联系上浙江东阳的一所木工学校,从上海自驾出发了。
上海距离东阳三百多公里,四个多小时车程,张默往后备箱里塞了几件耐脏的衣服、平时看不上眼的鞋子,还自带了一床被子。他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,“我不确定去那个地方能不能够找到答案,但我确定的是那里至少有路牌。”
一到木工学校,师傅来接他,还没等他收拾行李,师傅就拉着张默直接去车间干活了。在师傅指导下,对木工零基础的张默第一次花了三四个小时,用车床车出来一支圆珠笔套,再把笔芯套在里面,做出了一支笔。那天碰巧是师傅50岁生日,晚上大家伙聚在一起吃饭喝酒庆祝,十分热闹。
后来师傅才告诉他,这是他的策略。“因为这支笔零基础也可以上手,而且能够马上出一个漂亮的成品,勾住你的成就感和好奇心,如果上来就让你磨刀,磨四五天你肯定跑了。”
在木工学校,张默的身份是社会培训学员,学费是三个月9800元。说是三个月,其实也没有严格限制,他在那里一待就是近十个月。木材、住宿都包在学费里,每个月的开销不到一千元。
他开始审视以往的都市生活,“在上海拼死拼活的,一个月好几万,那时候就想花一大笔钱,让自己放松一下,透一口气”。
张默每天都工作到很晚,有时候花七八个小时打磨一个物件,或者用十天甚至更长时间做一把椅子、一张桌子。他享受这个过程。学木工之后,师傅曾经对他说,“人生很漫长,偶尔暂停一下其实也没什么。你可以更好地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,看看内心真实的想法,欣赏一下人生细微处的精彩。”
2022年6月,在第九届深港双年展上,人类学家项飙和青年策展人何志森联合发起了“看见最初500米”工作坊。招募来的学员需要在三个月的项目期结束时,把自己对“附近”的感受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向公众展出。
张默向工作坊投稿了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,写他待在方舱医院的几天,对方舱附近的观察。凭借这篇文章,张默从三四百人的报名队伍中脱颖而出。
2022年新年刚过,张默就飞到广州,展开关于“附近”的田野调查。几经变换,他选择落脚在广州老城区、西关一带,那边有很多物美价廉的老字号、老街坊,市井气息弥漫在古朴的骑楼间。
有一次,他在街上发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木匠,每天都在自己家门前的小空间做木工活。老木匠住的地方附近有一条古董街,老板收的老古董缺了零件,就送到他这里来修补。连续好多天,张默就蹲在旁边看他干活。
听完张默对老木匠的观察,项飙也觉得眼前一亮,他说,“你看他是在修复古董,我们在做的重构附近也是一种修复,修复社会。”
“修复”这个主题在张默心里扎了根,催生了他的“流浪椅子”项目。他发现老城区里有很多缺胳膊少腿的旧椅子、旧家具,就把这些旧物回收来修好,然后招募一些人来领养。他给每把椅子做一张领养证,记录这把椅子被捡到时候的样子、修复的过程。被遗弃的旧物,在一次修复和移交中,重新拥有了新的生命。“我是个木匠,修复不了社会,但我可以修复一些椅子。”张默说。
张默在修复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工作的意义。工作坊结束后,张默把“流浪椅子”从广州带回了上海。家楼下有一个垃圾站,成为他的固定“扫货点”。最近,他又在安徽歙县做大木作,一待就是数周。
张默发起了“流浪椅子”项目,把老城区里缺胳膊少腿的旧椅子、旧家具回收并修复,然后招募人来领养。(受访者供图 / 图)
“等待人生真正的春天到来”
拉拉渴望给自己找一个歇脚处。工作多年,她和丈夫一直计划着未来换一个节奏慢一点的城市。他们考察过很多地方,比如云南,但两人都不适应南方的环境。最后,他们决定就在北京的周边找一个能开启新生活的地方。
正式辞职的那一刻,这个筹谋已久的计划迅速落了地。拉拉最后锁定了北京延庆区井庄镇三司村的一个小院子。延庆紧挨着昌平,到市区大约一个小时车程。拉拉用几万元的价格租下了一个带院子的独栋房子和一块自留地,在离职后的那个冬天和丈夫一起搬了进去。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,“那个冬天好像一个筹备的阶段,好像一直在等,等待那个人生真正的春天到来”。
拉拉给院子起名“诗二三”,找来在泡泡玛特做设计师的朋友设计外墙涂鸦,在院子里种上蔬菜、果树。他们和父母一起在农家院里度过了第一个春节。樱桃成熟时,她邀请朋友们一起来摘樱桃、泡樱桃酒;丈夫喜欢骑摩托车,经常带着她在山上追逐羊群。
农村的生活有诸多不便,没有物业,水电暖不齐全。第一年冬天,气温零下二十几度,院子里的水管被冻爆了四五次,全都得自己修;电器短路、停电,也要自己解决。村里只有一个小卖部,他们只能每周开车去市区采购。
拉拉的物欲大幅降低,养车、保险、水电几乎构成了全部的生活开销。地里种的蔬菜能够自给自足,农村的两年,她和丈夫几乎没有买过衣服。在大厂时,她三餐都要叫外卖,点咖啡、下午茶是家常便饭,现在连一杯奶茶都买不到了。
村民们热情淳朴,邻居武哥一家和他们关系很好,手把手教他们种地,带他们融入当地生活。拉拉无意中提起,院子里要是有一棵树就好了,第二天发现树已经在那里了。还有一次,她想在院子里搭一个亭子,问邻居哪里能买到材料,邻居直接就把亭子搭了起来。直到现在,拉拉夫妇不常住在村里了,邻居还是经常帮忙收拾院子、打扫卫生。
西西和颜子车开发了一个有机农场,尝试把大厂的职场经验带过去。离职前,他们就在广州花都郊区租了十亩地。那时两人只想创造一个能在工作之余回归田园生活的休憩之地。但预想中短暂的待业期一再延长,变得越来越煎熬。春节过后,西西和刚失业不久的颜子车一拍即合,决定用这片农场干点什么。
他们从零开始学种果树。广州雨水充沛,野草长得很快,每个星期除草占了大部分的工作。农场种植了长果桑葚、芭乐等水果,每种都带来不同的体验:芭乐容易长虫子,在结果期需要用袋子把果子一个个包起来防虫;长果桑葚不易受虫害,但采摘期很短,刚结果时是青色,两三天就变红,再过一两天就变紫了,再不采摘,就变成黑色,熟透掉到地上。
“所以就会很着急,你看着那个果掉下来,感觉掉下来的都是钱。”第一批桑葚成熟时,他们在农场里收了整整两天。
大厂在他们身上留下很深的烙印。谈起农场,他们还是习惯性使用“碰方案”“迭代”“优化”“复盘”这些行话。他们曾经尝试卖鲜果,买了很多包装盒回来,发货给全国各地的朋友,试着“走一遍流程”,结果发现即便发了冷链物流,桑葚还是不能过夜。他们“迅速迭代”,又开发出水果干、手工皂、冻干粉。
类似的“试错”还有摆摊。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,他们刚结束了三天的摆摊初体验,顶着高温出摊不到半天就下起暴雨,不仅顾客寥寥,产品也都被淋湿了。摆完摊,又紧锣密鼓地开始复盘:销售成果不佳,他们客观地分析极端天气、场地“踩雷”、用户群预判失误等一系列原因,把经验分享在小红书上。
很多事情和以前不一样了,他们现在做的是“自己的东西”。“在大厂做运营时,每天就是盯数据,看盘、做复盘,但自己拿主意的成就感和给别人打工是截然不同的。有时你明知道这个项目做不下去,可能领导也知道做不成,却要跟他的上级有个交待,就闭着眼一起做,没什么意义。”西西说。
西西和颜子车在广州花都郊区租了十亩地,开发了一个有机农场,尝试把大厂的项目经验带过去。(受访者供图 / 图)
“像休了一个漫长的假”
脱产在家备考10个月后,奶盖考上了广州一家医院的事业编。她的职位主要是写材料、开会,几乎从不加班,也不再有KPI压力。“现在无论你干多干少,大家拿的都是一样的,主要看医院效益。”她说。
奶盖花了很长时间适应这种生活。在大厂三年,她参加了两次年会表演,穿着lolita裙子跳二次元舞蹈。但是在医院工作后,穿衣打扮要注意不出格。有一次,她做了一个颜色鲜艳的美甲,贴着大亮片,发朋友圈后,领导立刻私信她,要求她卸掉,理由是第二天有一个重要会议。
奶盖至今无法判断,离开互联网行业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,但刚毕业时对大厂的狂热滤镜已经消解。“就算我不离开,有一天我可能也会被淘汰。这个行业也要筛选,留下一些真正适合的人。”
在木工学校过了近十个月田园诗一样的生活后,张默已经感受到现实压力:房贷还着,公积金空了,的钱一天天在流失。后来,他接到了建筑修缮的工作邀约,但是经济压力始终存在。比起在大厂,他的收入水平大幅滑落,存款几乎没有增加,只能维持简单的生活开支。
张默有很多计划想实施,但都需要钱的支持,他还在继续探索,尽力从目前的资源和项目中寻找提高收入的方法。他不后悔当初的选择,“很多人会在忙事业的过程中忘了自己曾经的初心,放弃了曾经的喜好、爱好,都觉得挣钱最重要。钱是一个实现手段,但它肯定不会是目的”。
对西西和颜子车来说,失去稳定收入的压力也始终如影随形。西西喜欢中古包,以前每年会花几万元买包,每个季度都要去旅行。现在有了时间,反而不去了,因为机票、酒店都很贵。颜子车刚刚成家,背着房贷,他开始习惯自己在家做咖啡、烘焙,减少出去看电影、吃饭的次数。
农场很难短期收回成本,进一步运营还需要投入更多,包装、设计、产品、销售,每一步都需要钱。他们尽可能压缩成本。创业园的工位租金太贵,他们平时就在园区里的咖啡厅办公。冻干机是向工厂借来的,如果自己购买,即使是小型家用的冻干机都要两三万元。为省下设计费,画插画、拍产品图、设计包装、做海报,他们全部亲力亲为。他们还设计了很多方案,开农家乐、做亲子研学项目、出售农场手作,但这些都需要更多资金。农场的厕所是他们用砖头搭起来的茅房,也没有修路、铺草坪。想要修缮路面、像样的厕所,也需要钱,而面对越来越审慎的投资者,一个漂亮的方案PPT似乎很难说服他们买账。
他们一边经营农场,一边继续投简历。“其实两边都有盼头。一方面我们想争取把农场做大了,就不需要找一份之前那样的工作;但这可能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它是一个爱好,但这个爱好不能养活自己,所以还是要想办法去找钱。”
在互联网行业辗转十年的西西聊起被动离开大厂后的落差,已经表现得很坦然,“摆摊啊,开一下滴滴、跑一下外卖这些,肯定有的。大家只是不说而已,因为还是很没有面子的”。
虽然拉拉很适应在农村的新生活,但丈夫一直水土不服。他需要社交,村里大多是空巢老人,他只能和村里的高中生打打篮球。每周回市里探望父母、朋友时,他总是格外兴奋。后来,丈夫开始准备社工考试,他多次暗示拉拉,即使没有通过考试,他也想回去了。
他们试过把小院开成民宿,让它热闹起来,同时弥补失去收入的焦虑。但疫情期间民宿的收入并不稳定,还要面对状况百出的客人。曾经有一个老人,在民宿喝得酩酊大醉,从楼上吐到楼下,还非要拉着他们一起喝。她也遇到过“熊孩子”,把房间的墙壁涂得惨不忍睹。
2023年初,丈夫考上社工,去了社区工作,拉拉则在机缘巧合之下回到了原来的岗位。过去的两年,用她自己的话说,“像休了一个漫长的假”。
再次回到城市后,拉拉的小院至今还在出租,他们每周都会邀请不同的、遇到各种烦恼的朋友去小院里过周末。拉拉希望这里不仅是她和丈夫的曾经的避风港,也能够治愈更多人。
(应受访者要求,拉拉、奶盖、西西、颜子车为化名)
其他人都在看: